如果现在把手伸进我的工具包,一路穿过轻巧的验电笔,沉重的摇表,表面粗糙的手电筒,便会摸到一小块沉甸甸的不规则废铁。这是我的纪念品,我死里逃生的见证,我一碰到它,它便冰凉凉地刺我一下,像一团冰冷的湖水,带我重回那个夜晚。
那是我刚工作两年的一个晚班,那时益阳电厂还没有并入陕煤。我们班接到就地通知,有一处临时电缆着火,等我和班长拎着灭火器跑到时,明火已被用沙子压灭,只剩几缕青烟从桥架缝隙里钻出来,在应急灯下拉出扭曲的影子。
“把烧断的电缆剪掉!”班长对我喊话。他指着我身前一段外皮碳化的电缆,黑色塑胶剥落处露出焦黑的线芯。我蹲下身,膝盖硌到一块发烫的电缆皮,手套触到的桥架表面还带着余温。让斜口钳咬进电缆的瞬间,钳口与线芯接触的刹那——
“砰!”
不是爆炸声,更像高压电线短路时的闷响,空气中瞬间炸开臭氧的味道,一道蓝紫色弧光突然从钳口窜出,像条活蛇猛地扑向我的手背。本能让我往后仰倒,斜口钳脱手而出,砸在两米外的槽钢上,发出沉闷的当啷声。我撑着地面往后挪了半米,才敢抬头看:那把刚领的斜口钳,原本银亮的钳口已熔成一团不规则的疙瘩,还在嘶嘶冒着白烟——它做了我的“替死鬼”。
“你怎么不花点时间确认有没有断电?也是倒霉,都这样了空开怎么没跳!”班长的吼声带着颤音。说不清我是怎么回班里,只记得大冬天里,我坐回椅子上才感觉到凉意——贴身衣物早已被冷汗浸透。下班路过衣冠镜时瞥了眼,脸色比贴着安全警示牌的墙面还白。
第二天,我便请假回了云南老家,没过几日便要过年,母亲也只当我提早归家,我对事故只字未提,只是往床上一倒,陷入了昏沉梦乡。再醒来时,家里弥漫着一股鸡汤的浓香,母亲在厨房压低声音打电话:“……他脸色不好,是不是在单位受委屈了?”我静静听着,躺在床上良久,有种想哭的冲动。饭桌上,母亲小姨问些工作上的琐事,我也一一回答。电力人的假期总是有限,过了几天,我又回湘,站台上母亲说:“怎么才回来又要走,路上注意安全!”我隔着玻璃看她,心里难过,母亲一手把我带大,我们相依为命,没有我她该多伤心啊!不敢细想,便把头埋了下去。
回岗后,我留下了这把斜口钳,从此,每当“快一点”“偷点懒”的思想一冒头,伸手碰到包里的冰凉的一块,这些念头又缩了回去。安全,实乃立身之本。亲身经历过才知道,电气安规上那句:“任何电气设备在未验明无电之前,一律视为带电”是多少血与泪的教训!
此后的我,收起了几份轻松玩笑,打起了十二分精神,面对工作多了许多敬畏:违章操作便像与天在赌,只是赌注和奖品太不成正比,天秤的一端是人的生命,而另一端只是几分甚至几秒的时间。
安全为了谁?朋友们,安全是为了自己,也是为了你所珍爱的所有人,为了空荡荡的餐桌有人落座,为了千万里的思念能够安放,我们的生命并非孤岛,它牵连着骨肉至亲。生命宝贵,安全是责任——这是那把替我“送命”的斜口钳最后、也是最严肃的箴言。( 长安益阳 黄雨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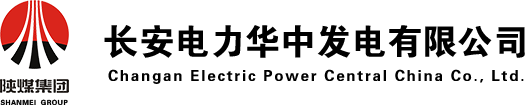


 友情链接:
友情链接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