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久以前的某一天,一粒种子偶然落到了这个地方,风吹起尘土,一点一点将它盖住。然后下了一场大雨,接着太阳出来了,阳光暖暖地照着,土里又温暖又湿润,这种子发芽了,它就在无人的地方悄无声息地长着。等到人们发现这里有棵树的时候,它已经长得有几米高了,人们觉得它长在这里也不碍事,就由着它长,终于长成了一棵大树,枝繁叶茂。孩童们喜欢在树上树下嬉戏打闹;村民们下地,如果碰到一场急雨,就会跑到树下避一避;三伏天的正午时分,太阳当空照着,热浪一阵阵袭来,下地的村民们也会带着自带的干粮,坐在树下,填饱肚子,然后躺在荫凉里睡一觉,为下午的劳作养精蓄锐。
后来大家觉得在这里无端的长了一棵树,且树干笔直,枝繁叶茂,即使接连几年不下雨,大树枝叶也不见干枯,此处必定风水不错,便决定在这里打一口水井。村里各户人口各出一个劳力,开始挖井。不出所料,打了四五米深,便有水涌了出来。又清又甜,用井水酿出的酒醇厚浓郁,用井水泡出的茶回味幽长。
当启明星还在东边的天空闪烁,就有人在井边出现。最先来挑水的小媳妇们每天在这个时候聚在一起,家长里短一番,然后挑着水各自回家,准备一家人的早饭,让家里的男人吃饱好下地干活。白天,偶有旅人经过,取水解渴,坐在树下休息一阵,又离开,不知那人从何而来,也不知去向何方。日暮时分,归家的村民们牵着牛经过这里,先让牛喝饱清凉的井水,自已坐在井栏旁抽着烟。有晚风吹过,树叶沙沙作响。
一年又一年过去了,井口长了青苔,成了老井;树越长越粗,成了老树。从井口可见碗口粗的树根贴着井壁扎向土地深处。雨水多的年份,井水也不会溢出,干旱的年份,井水也不见下落。大树老叶落下,新叶长出。水不盈不亏,树四季常青。
人是一天天的过着,树是一年年的长着。人每天都做着相同的事,树每年也经历着同样的季节,人的一日三餐和树的一年四季交织在一起。人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树春天发芽秋天落叶。人经历的时光日复一日印在脸上,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;树经历的时光一轮一轮变成年轮,树越来越粗。石头砌了一圈的井口,有被井绳子磨出的痕迹。厚厚的青苔被水气滋养,长得越来越厚,把井口一圈都染绿了,又四处漫延,连树干朝北的那面也被青苔覆盖。
因为这棵老树和老井,这个村子成了宜居之地。村里的人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,村落变得越来越大。村里不仅人丁兴旺,就连牲畜也繁殖得极快。春天来临时,村里每家每户的猪圈就会多出了十几头仔,田野里每头母牛后面都跟着一小牛犊,一只只母鸡一边带着一群群小鸡啄食,一边警惕地不时抬头张望,生怕一只老鹰或黄鼠狼把小鸡叼走。村里阡陌交错,鸡犬相闻。
时光流逝,当年那些挖井的人一天一天地变老,死去,他们便永远地留在了这个村里,留在了那段属于他们的时光里。当他们的儿子孙子也老去,死去后,便没有人记得他们了。年岁久远,最后他们的坟头被风雨削平,墓碑也被抬走,搭在了一条小水沟上,人们要过这条小水沟时,便不用使劲一跨,顺顺当当便可过去。后来的人们在这棵树下纳凉,在井里打水时,想不起培树挖井的人,只有这口井记得,这棵树也记得。
时光流转,春去秋来,每年都有接亲送亲的队伍抬着大红的嫁妆从这里经过,村里有姑娘嫁了出去,也有外村的姑娘嫁了进来。每年都有几支披麻带孝的送葬队伍在唢呐鞭炮声中送走一个人,也有接生婆慌慌张张跑过,去迎接小生命的到来。村庄吐故纳新,生生不息。有人年少时离开村庄,远去他乡,在颠沛流离中,家乡的老树老井夜夜出现在梦里;也有人十几年后衣锦还乡,在村里建起层层院落,气派非凡。有人一去再也没有回来,从此沓无音讯,家里亲人日盼夜望,最终也没有盼到归人。也有人年少离开,再回来时只是一方盒子,人们把他安葬,从此他再也不会离开。
只是平常的村庄,人们过着平常的日子,日升日落,春去秋来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树几百年了还在,井几百年了也没干。但对于每一个经历人生这场大梦的人,短短几十年的日子,不管是风和日丽,或是凄风苦雨,都要独自面对。好在有老树炎热时为他提供清凉,风雨时替他遮风挡雨,有老井的水源源不断,为他解渴。老树老井见证他的欢乐或悲伤,看着他从婴儿变成老人,走过人生四季。人是在一个偶然的时间降生在这里,活着,又在一个必然的时间离开。只有老树老井,一直都在。
有千百个这样的村庄,有千百颗这样的老树,有千百口这样的老井。一个村庄的故事,也是千百个村庄的故事。千百棵老树,千百口老井,像是同一棵老树,同一口老井,出现在人们童年的梦里。(成白岚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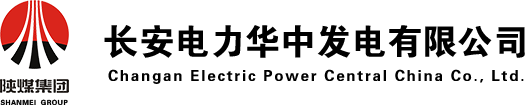


 友情链接:
友情链接: